偶爾在重重山水的逼仄下,多少個青春從眼前匆匆露面,更多的時光也已經逃逸不見,于是在悲憫的作用下,竟也會想起來當初清純的自己。
如果是這樣的話,一切的變化都是變異,便不算一樁好事了。恁多卻有限的生命中,永遠都發展得參差不齊。要是可以,奔放着的,又有誰喜歡過拘束,又有誰願意一語不發,苦于牗下兩三年之長久呢?大概時空是無情的,更多的成了克制與壓抑而不是疏導與打通——這是頗為可惜的,但也難以下手了。
如果不能下手的話,這也是假話,無非是泛泛而談了。可憐我們的孩子,五六十人?七八十人?或許是九十上百,極其狹窄的教室内、極其簡單的設施裝備、極其簡樸的飯菜飲水,卻有笑聲哭聲、讀書聲、吵鬧聲、掰動指節的滑聲、刀子刻在桌上的摩挲聲、夏熱冬冷聲,而且終日不絕,他們依舊安好着,在拘束的天地外盡量能夠維持我行我素着。
這是頗令我感動的事情,也生出無限感慨來。大概最好的就是這樣,各種環境,不論條件,依舊守着骨子裡最純正的性子與習慣,于是天南地北,各赴東西,他們頑強生存着,豈不知無有生死?豈不知無有酸甜苦辣?
我常常回憶起身着淺藍色校服的那群孩子,他們躺睡在校車旁,乘着還有的一些樹蔭和光明;也有的索性靠在樓梯旁,等着同學來叫醒他——這些孩子,我稱之為孩子,我大概是下淚了——可是曾經嘴角殷紅的血,難以撫平我們這些隻能勉強稱得上執筆人的心了。
大概世界本無所謂富貴貧賤,更無何優劣等級之分。偶爾時機下的相逢——如果硬要用緣分的說法,那苦抄過萬字的他竟也毫無怨言——多少這樣的事情随着流光,就甘心藏于他人眼底身下,一直默默不作聲,實是我們不能比較的。
相冊還保存着一張初三時的照片,戴着黑色鴨舌帽,低着頭,背景有些許的曝光,在運動場的邊緣,在初冬的寒暄中。清純時候的自己,和他們一樣,沒有困乏,沒有真正的惡作劇,寝室燈盞下的訓斥聲,粗茶淡飯催使下的跑步聲,我漸漸明白,深秋已經徹底遠離,我們都得這樣生活,背景有些許的曝光,在運動場的邊緣,在初冬的寒暄中。
一張自行車,曾經就是我們的寶物,到現在擱置一角,直到鏽迹斑斑無法騎動才敢宣布青春一季的過去,一聲招呼,一次點頭,我還是不願承認,在他們的稱呼中被動更改了自己的身份,更不希望,有任何超過他們的可能,過去乃至于未來。
我可能已經知曉,老百姓的生活都是這樣,曆代的流傳與變化中,老百姓他們可愛的兒女,亦何嘗不是如此。就是這樣,過去乃至于未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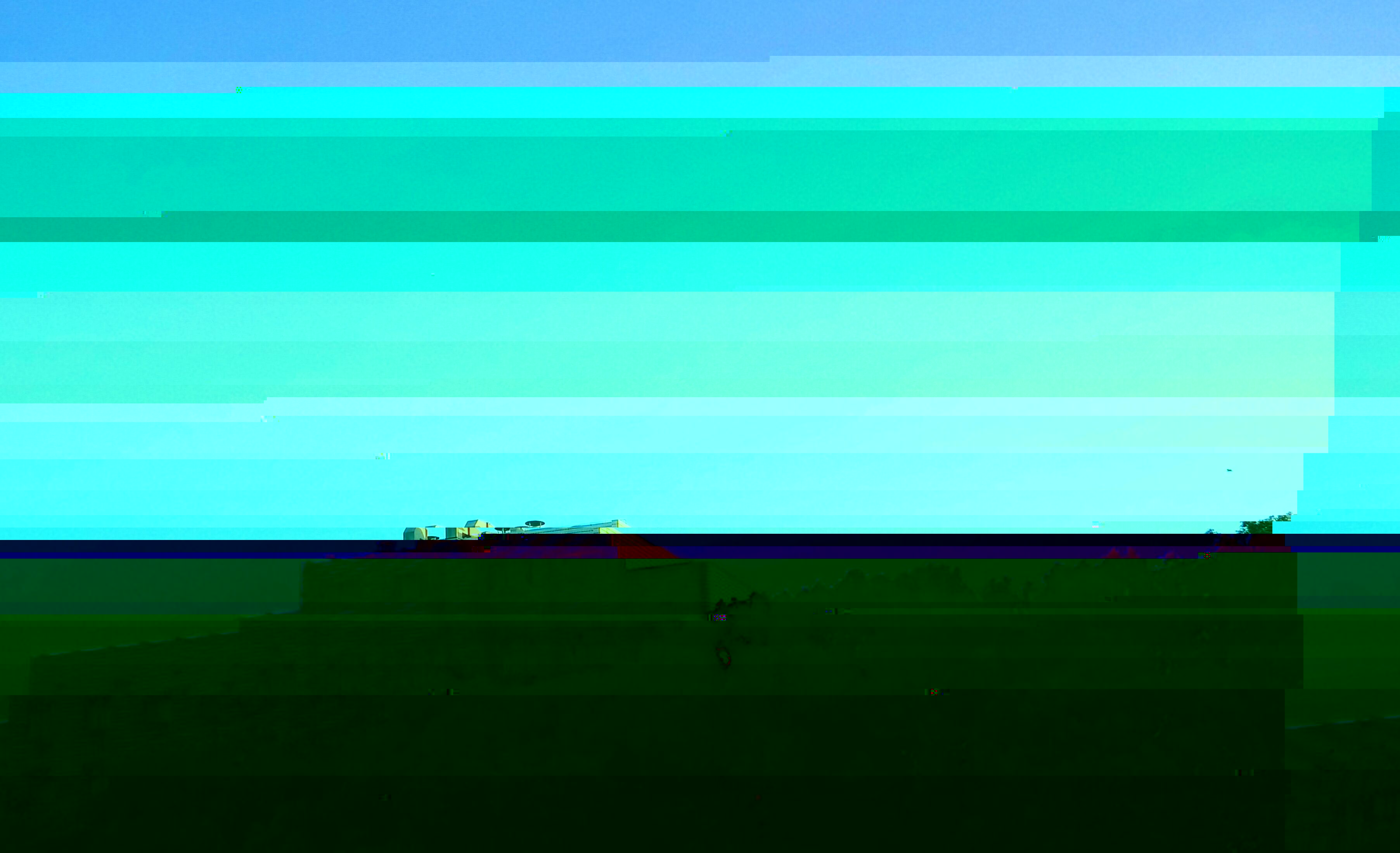
文/劉法鑫
21級文學一班